发布日期:
永远的异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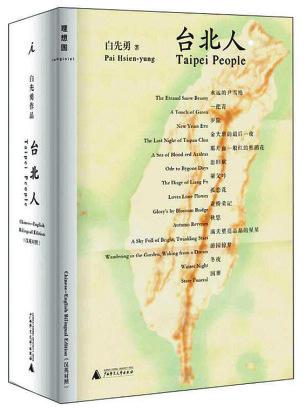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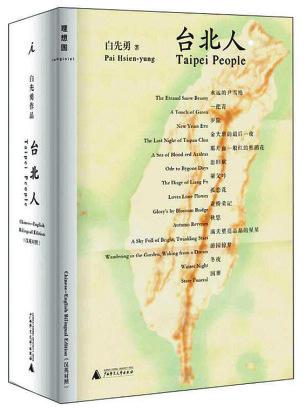
《台北人》
白先勇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一批20世纪从大陆“逃难”到台北的人,他们身份不一,有舞女、知识分子、军人、军人家属、企业家、工人等,既有曾经身份显赫的社会上层阶级,也有依附于他们而生存的小人物。他们在大陆时都各有各的意气风发,而在台北又各有各的落魄失意。
十四篇文章,有远不止十四份失意。《一把青》中小朱青腼腆羞涩,而“台北的朱青”成熟世故;《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中金兆丽不得不屈服于现实嫁给一个从前上海滩的“玉观音”决看不上的男人;《岁除》中的赖鸣升念念不忘的是从前在大陆当兵的岁月;《国葬》里的秦义方对过去的沉迷和对现实的拒绝。还有许多,便不一一例举。
这些人从大陆迁徙到当时百废俱兴的台湾,他们念念不忘的是记忆中1949年前的大陆,沉湎上海、南京、桂林等地。
他们内心充斥着无法排遣的孤独,这种孤独感使他们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沉浸于辉煌的过去,排斥落魄的现在,无法排遣孤独,只能一直回忆往昔。
孤独到了最后,不免沦落到死亡的地步。《台北人》中便有不少的“死亡者”,《一把青》里的郭轸、《花桥荣记》里的卢先生、《永远的尹雪艳》里的徐壮图、《梁父吟》中的王孟养等。这些人死亡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患病、自杀、飞机失事、原因不明的猝死……
沉心思考,尽管他们死亡形式不同,但是造成他们死亡的终极原因却是相同的。在捉摸不透的命运和无法改变的历史驱使下,孤独的台北人找不到现实与过去,生与死的平衡点,最终以“死亡”来解脱自己。
《台北人》一书中散不进的孤独感,让我对作者也产生了好奇,了解以后发现这种孤独感与作者白先勇是离不开的。他出生于乱世,年少时饱受过疾病的折磨,失去亲人与爱人,有过客居异国的经历,人生中许多阶段都与孤独作伴,也许正是这样他才能写出这样出色的文字。
忙碌的课业之余,不妨偶尔一读令人沉静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