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行者无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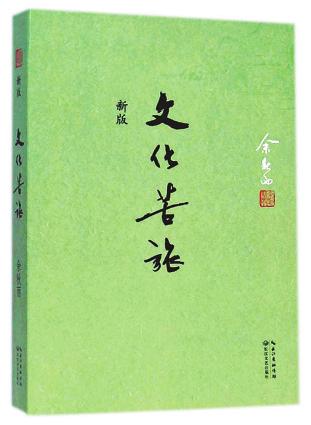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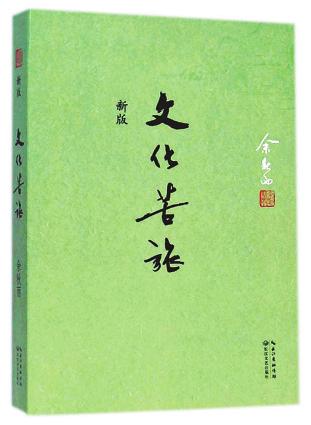
《文化苦旅》
余秋雨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如梦童年”是全部苦旅的起点,是自然和精神意义上的开始。童年可以“如梦”,长大后步伐踏实,便开始了以成年人的目光和脚步所抵达的中国之旅。在这段旅途中,我们耳听辛弃疾等人笔尖的铁马冰河,触摸着朔风中壮美的阳关雪,感受着沙原隐泉的清洌可鉴,在莫高窟的壁画前体会宗教与艺术的色彩,在西域喀什领略各大文明的交流与融合。改变“阅读视界”,看杭州西湖的水光山色和阴晴寒暑,悟“赤壁怀古”的大气磅礴与超然洒脱,品宁古塔的艰难困苦与高贵人格,在时移世易中与晋商一起探寻“士农工商”的定义,在“天一阁”浩如烟海的藏书中斡旋生命的脆弱与文化的渴求。在这段“托体同山阿”的旅途中,我情不自禁地感慨中华文脉的源远流长,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文化在发达之后,根子上仍然是生命的痕迹”。
“拜水都江堰,问道青城山”,余秋雨先生认为可把“拜水”和“问道”当作一件事。“水”不仅意味着生命的孕育,也体现在四百毫米降水量分界线塑造的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更划分了中华文明的三条天地之线,即黄河、长江、长城。加上东部的大海、西北的沙漠、西到西南的高原,中华文化以海纳百川的姿态拥抱着世界。我们常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余秋雨先生认为“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天地给了我们生存与文化的基座,而人类渺小,是难以强得过天地的。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要讲文明之道,唯一的道就是自然,中国文化在最高层面上是一种减法文化,是一种向往简单和自然的文化。
行者无疆,欲在世界文明的坐标中反观中华文明,就需要踏上寻访更加辽阔土地的世界之旅。对比外国文明,中华文明缺乏了一种宏大而强烈、彻底而排他的超验精神,却保持着一种实用理性。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我们自古强调平衡、适度、普及的价值观,这也使得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延续,焕发生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当然也造成了中华文明一定程度上缺少对大海的亲近,但中国人却不曾停下走向海洋的脚步。前有河姆渡、良渚或许更久远年代乘风破浪从中国出发的无数小船,后有我们所熟知的鉴真东渡、郑和下西洋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可见,中国人从来不缺乏开拓精神,他们作为“漂泊者”,把中华文化的种子撒向了全世界,并且仅以和平的方式,这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是绝无仅有的。
中外文化因为世殊时异和地域之分有诸多不同,却也有相通之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亚里士多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虽然表述方式有所差异,但都传递着对知识与真理的向往。康德断言人类基于自己的理性,一定会克服对抗而走向和谐。众所周知,当今世界所面临的大多数灾难,已经没有了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诚然,各个文明间都可能产生冲突,但事实上,“山川异域,风月同天”,21世纪的最根本冲突,产生在文明与非文明之间。目前全人类共同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也说明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守护人类的整体文明,是迫在眉睫的当代大道。
“Theyhavesaid.Whatsaidthey?Letthemsay!”是萧伯纳写在壁炉上的三句话。这几句话漂洋过海开启了一段“人生之旅”,虽历尽沧桑,却拥有不被时间淡化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让我想起了鲁迅《自嘲》里的那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沉默不是沉沦,而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勇气,是陈寅恪口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吾日三省吾身”的为人处世姿态。于是,我不由得经常告诫自己,“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走得太快了,不要忘记当初为什么而出发。
“即使身陷沟渠,也要仰望星云”,据说这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挂在办公室墙上的一句格言。余秋雨先生说,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在睥睨万物,却很少有人会抬头仰望,因此,出现了太多高楼的城市,反而低了。我们常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但如果脚下的不是实地而是泥潭,我们是否还能仰望呢?在逆境中仍旧不改本色,不忘初心,是一种更为高尚的人格,它产生于忧郁,来自于思考,终归于安静,我开始明白“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含义了。
踏上这段“文化苦旅”,起初我的注意力聚焦在“苦”上,认为“苦”是一种常态,人在旅途,有舟车劳顿带来的疲惫之苦,有人生地不熟的迷茫之苦……实在难以全数列举。而如今我更为关注“旅”这个字,大家常说“身体和灵魂必须要有一个在路上”,然而身体和灵魂又怎么分得开呢,它们二者总是同时在路上,就像路和书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书即是路”,于是我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内涵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行者无疆,我愿在这段“苦旅”中寻找人生的诗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