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大千世界在浮躁的气团里五光十色——重读贾平凹《浮躁》有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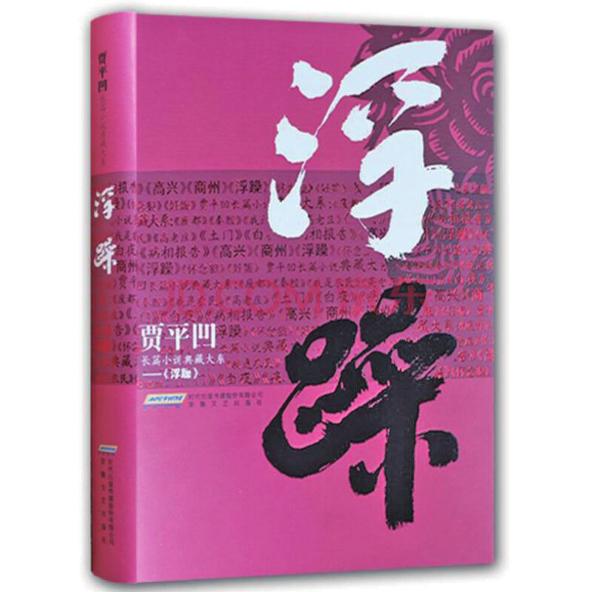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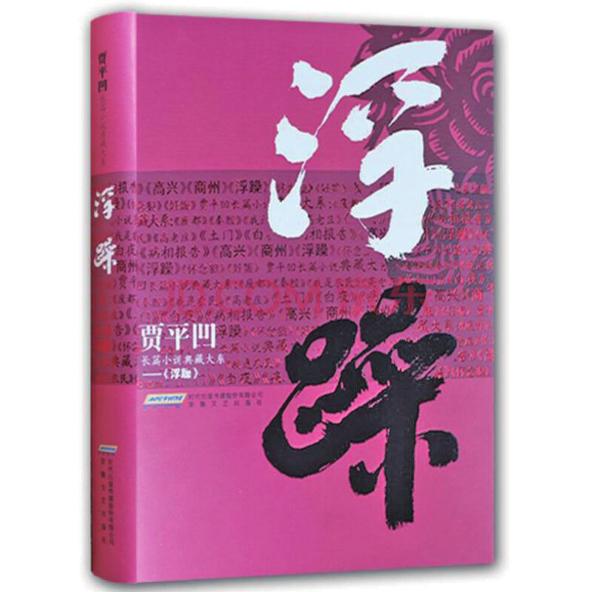
如果说狄更斯《双城记》里“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是一种定位式的判断语句,那么,在贾平凹长篇小说《浮躁》的序言里,则是以一种平静的陈述语句表达了对时代的态度——“不需要作过分的赞美,同时亦不需要作刻薄的指责”。
在贾平凹那里,“浮躁”一词该是没有太多“贬义”在其中的,他只是从他“商州”地域历史的站位开始,试着把握住了“浮躁”的时代情绪,经历过了“妊娠”的时代阵痛。
他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在当时并不被大多数人体察的,过后则明了矣。要写出生存在其间的当下的时代,作家只需“真真实实写出来,混混沌沌端出来”。这种“真实”与“混沌”,看似矛盾实则是一体的——真实并不是清晰可辨的,混沌也不是有失原形的。
在变革的年代,当一切都处于浮躁的阶段,贾平凹用他超前与超敏的触角,体察到“旧的东西日日剥离,新的东西日日再生,惊喜惶惑,适应,创造,大千世界在这浮躁之气团里,呈现五光十色”——而他的真实,就是写出它是如何“剥离”与“再生”的;他的混沌,就是呈现出它是如何“五光”与“十色”。
《浮躁》是贾平凹唯一在开篇写了两则序的小说。与其后多部长篇的后记相通的是,他都在其中阐述了自己不一定熟虑、但必是深思的文学观。说不一定熟虑,是因为贾平凹的创作,一直都是在不断探索与挑战中的,他没有给任何时期的自己一个定式——从“我的这条州河便是一条我认为全中国的最浮躁不安的河”这句话开始,便可以代换式地理解为,我认为“中国这条河正经历着它上下五千年来最浮躁不安的时刻”,“我的文学艺术之河也正经历着最浮躁不安的流变”。
他一边预言着时代的前途是越走越深沉,越走越有力量的,一边又在序言二中,宣布着将再不从事《浮躁》类的写法,理由是: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自此,他在自己的一脉上分支而去,要“以自己的存在流,以自己的经验流”。
他一边认识着“人的主体意识的高扬和低文明层次的不谐和形成目前普遍浮躁情绪”之因,也一边感应着时代“水波兴动”之果,于是,他让主人公金狗给雷大空写出了这样一句精准而又磅礴的“时代祭文”:
泥沙俱下,州河泛滥而水大好行船;浮躁之气,巫岭弥漫而山高色壮观。
这“水大好行船”的实用与功利,让各种欲念泥沙俱下而无沉淀,这“山高色壮观”的空蒙与虚茫,让团团浮躁之气氤氲而无升腾。
如果说在1986年夏的《一点感悟》中,他还乐观地表达着,“我们的社会在浮躁着,我们的作家也在浮躁着,浮躁虽不是成熟的表现,但浮躁是前进的必然一步”。可到了《废都》,他却让庄之蝶给唐宛儿剖白:
这样我还能写出好作品吗?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心里却又焦急,怨天尤人,终日浮浮躁躁,火火气气的,我真怀疑我要江郎才尽了,我要完了……
此时,评论家评说《浮躁》时所说的“十分自觉地把笔墨放在展现中国当代社会文化心理形态上,社会心理的挖掘,社会情绪的把握,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依然适用而妥帖。
而后的《土门》里,他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坐在了明式的椅子上,我把我的下半身托付给了椅子。我又仰躺在明式的花床上,我把我的全身托付给了床。但我浮躁起来,翻身拳打脚踢椅子和床一通,走出了家门。
坐下、仰躺、翻身、拳打脚踢,生命在一段“托付”之后,他选择了再次“走出”,走出到哪里,又能否脱离浮躁转而脱胎出一种崭新的生命状态呢?
步入了醇熟之后的贾平凹,有一幅题为“大河流过我的船”的绘画作品。作品中,他打破了常规经验里,船在河中行过的状态,而是让“我”和“我的船”在一副“我自岿然不动”的气势下,任由大河流经。这其实有“自画像”的意味在其中:画中人随船入河,背手而立,信首昂扬,两岸块石磊磊,豪木森森。
如今,州河大水中的“地气”仍在升腾,大千世界也仍在浮躁的气团里五光十色。但贾平凹在“浮躁”之后,静中开花,对空数尘,不断地在自我突破中,向我们记录和展现着——每一个时代的洪流过后,沃土上的大树是从如何长出地面,如何突破浮躁尘埃,如何一日一日高大,如何聚起一股蓬勃豪气,最终长出崭新的生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