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微言之外境深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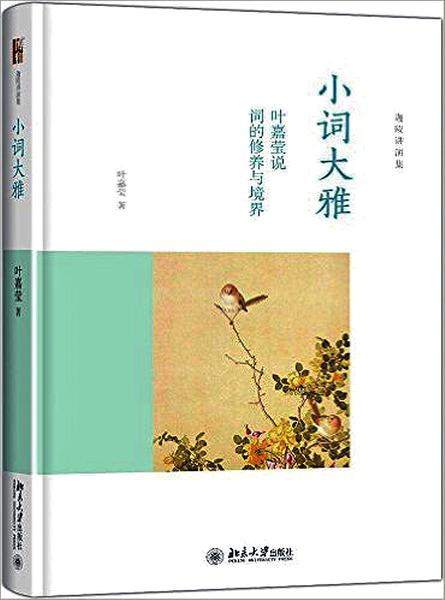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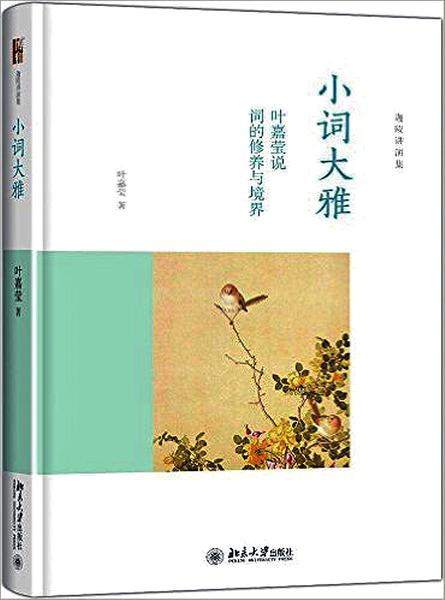
◇俞耕耘
小词不小,可蕴藉,微言非浅,境深沉,这是初读此书而生的直感。这本书根据叶嘉莹先生的讲演整理而成,因而它既是可读的,更是可聆听的。作者的声情言笑可谓尽在文字之中,我们既是读者,也是讲座现场的“听众”,它把我们带入小词的世界。单以书名论,小词大雅四字辞约意丰,耐人回味。它打破了古典诗学“诗庄词媚”的惯有眼光,也象征着雅俗合流,小词也能达到诗的雅正品味与精神内涵。
此书之所以立意清奇,在于它为小词“翻案”正名。正如闻一多在《唐诗杂论》中救赎了“宫体诗”,作者深感小词被视为艳曲小技的不公待遇。她以细腻的文本赏析,深沉的生命体验,宏阔的词学洞见,让我们聆闻小词中的修养与境界。
它既延续了古典诗话“以诗释诗”的传统,以诗论词,入木三分,同时又置小词于当代人的生活语境中。如作者将自己、女儿及学生的点滴生活体验融入对李后主词的理解中,让我们发现小词更是一种贴近生活的审美日常化。这也是古代词论无法实现的。
那么,应该如何发现并阐释小词的修养与境界呢?作者提供了一套品评小词的方法,依我看来,它可归纳为词论与创作,作者与读者,身份与性别,小语境和大背景的合一。当你做到了这“四个合一”,自然会独具眼光,更好发现小词言外的意蕴。
在书中,作者分析了张惠言与王国维两位词论家的词学见解。同时,你会发现作者“以西释中”,“中西互通”的深厚功力,既总结了二者的评词得失,也形成了她独具阐释学与读者反应批评风格的词论。正因如此,作者论词达到了上述“四个合一”。
张惠言的“兴于微言”是看重小词“言外”的比附深意。作者认为,他从温庭筠《菩萨蛮》中看出“感士不遇”的言志抒怀,颇有道理,并非牵强。作者更是用张惠言本人词作论证他自己如何“兴于微言”,这样不仅增强了说服力,同时也将“词论与创作”,词人与经学家的“双重身份”完美合一。作者举“花外春来路,芳草不曾遮”,“莺燕不相猜”,“何必兰与菊,生意总欣然”等词句,说明他表面写及春色,实质是在劝勉学生:追寻要看重内心方寸之间,不必外求;不为春色诱惑所乱的宁静,只要自我成就的平和。这些都是小词微言外,张惠言儒家修养的呈现。
王国维对张惠言的批评,正在于他没有重视“小语境与大背景”的合一。作者认为,温庭筠词中“娥眉”“画眉”“懒起”等语汇在历代诗歌中早已形成具有确切隐喻功能的指代系统。在这种系统中,男性也许会虚拟“思妇”“怨妇”来幽曲表述“私情”,自然会造成作者所言“双重性别”的合一。微言也可用西方文本的微型结构来解释,它成为一套来自传统的文化符码,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与一致性。同时,即使以温庭筠自身所处离乱衰颓的时代背景看,张惠言的阐释也有其合理性。
叶嘉莹认为,他们二人评词的不同见解实质是一个接受美学意义上读者反应的问题。她从解释学的角度出发,讲解了王国维“境界说”的妙处。境界是对小词高下品评划分的依据,我们看到书中列举的“美人迟暮”“众芳芜秽”“三大境界”的评断,是王国维作为读者自身的“断章取义”。作者用西方“阐释的循环”来说明,读解小词又受制回归于读者自身的经验、学养和知识背景。在我看来,如果以解释学中“视域的融合”来说明,或许更好。王国维有他的“个人视域”和“读者视域”,词作者有“历史视域”和“作者视域”。读解小词就是个人与历史,读者与作者视域的融合。
作者发现,王国维“在神不在貌”的观点对于小词“境界”评点具有关键性意义。他从侧面说明,小词不因题材和体裁而分出高下,关键是有没有精神追求和气象格调。你可以写男女情爱,也可以伤春悲秋,但是要有“高格”。这个境界,王国维本人是定义不清的,然而作者却从他对晏殊、欧阳修、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的评点中,看到小词境界的必备要素;即由人一己之真情生发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张惠言的修养、王国维的境界与作者的中西互释三位一体,告诉我们小词虽小,修养却深,题材虽小,境界却高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