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捎给生灵万物的“寓言”
◇方笑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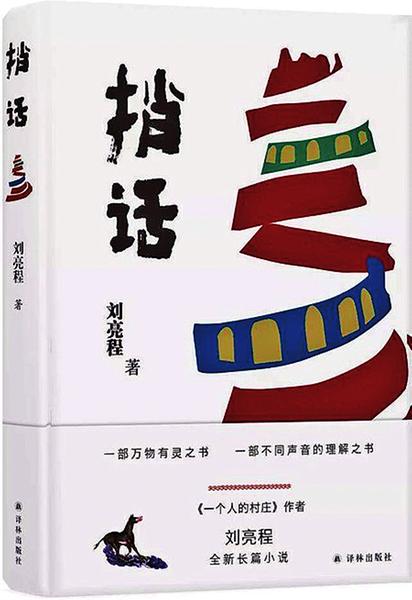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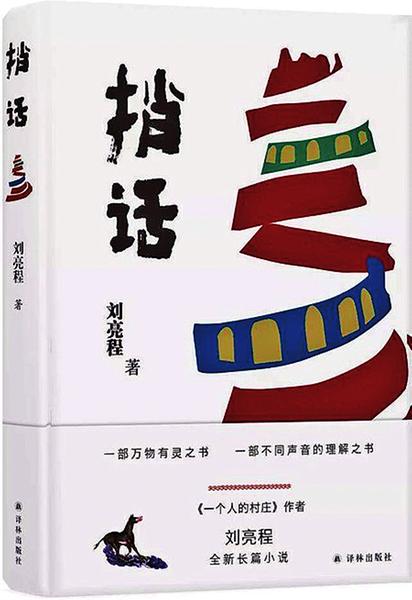
《捎话》
刘亮程 著
译林出版社
一片沙漠戈壁的战场,两种信仰的芸芸众生,数种生灵鬼魂的语言……刘亮程在千年前的天地间搭好舞台,一人一驴登台上场,背负“捎话”的任务,见证了茫茫历史与惶惶生死。一部长篇小说写完撂下笔,小说家这个“捎话人”,也就算把话给读者捎到了。
《捎话》问世近两年,刘亮程曾说他是“用千言万语,捎那不能说出的一句”。这部奇特的小说,是“一部人、畜、灵共居的乡村史,一部另类的人类战争史”,也是“一部对声音(语言)的理解之书,思考之书”。而相对于他一贯的写作风格来说,这是一部孤悬于现实和历史之外、捎给生灵万物的“史诗性”寓言。
《捎话》的故事本身并不复杂,在一段架空的历史时空中,一头叫谢的小毛驴,被一个叫库的翻译家牵着,当成一句话,捎给了千里之外敌国那个已改变了信仰了人。令人惊叹的是,文本中涉及到了战争、语言、历史、信仰、自由、束缚、灵与肉、人与社会、人与动物等多种主题,且许多寓意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从开篇的缘由,就有着荒诞的意味——毗沙的西昆寺内不能养驴,而昆门徒出行离不开驴;驴只能在寺外北坡下,但驴叫太吵盖住了诵经声;西昆寺修起高墙为挡住驴叫,而修墙的砖全靠毛驴驮来;毛驴驮砖累死不少,却依然鸣叫不止,墙也就垒个不停;后来,驴被人的倔强吓住不叫了,但墙还在往上垒。于是,“毗沙和黑勒,是东西方势不两立的两堵高墙,他们都认为对方挡住了自己(的太阳),都发誓要把对方推倒。”战争从此开始。
这样的缘由里,能想到的是什么呢?信仰的声音被无端遮盖、自己的牢笼是自己建的、东西方的矛盾始于高墙与太阳……这些,都是作者没有说出来的,并且,小说中不断提及捎话人只捎话,不捎变成文字的语言,因为话一旦变成文字就死掉了。语言文字背后的意义,就像战争的双方,互换视角,根本没有真正正义的一方。
战争的双方语言不通,信仰不同,人与动物,亦是如此。在人的世界里毗沙城是城,在驴的世界里,这里就是一座大驴圈,累死了几十代人几百茬毛驴修好的大驴圈。“驴高高兴兴住进去,割驴草、清驴粪、梳驴毛、钉驴掌……这些活儿都得人干,驴只动动嘴和蹄子,就行了。驴说,人真是个好牲口啊……”对于一个持有“万物有灵”观念的写作者,刘亮程自《一个人的村庄》以来,在乡村叙事的宇宙观中,不断与生灵万物交感、互通。
一种语言就是对另一种语言的闭塞,一种生命就是对另一种生命的倾轧,一种信仰就是对另一种信仰的亵渎。“你每学会一种语言,就多了一个黑夜。”于是,刘亮程以巫师般的“念力”,在语言的黑夜里打转,以荒诞色彩和梦幻气质,以不动声色的幽默和充满哲思甚至有些残酷的诗意,酝酿出一则饱满、丰富、意味无穷的寓言。
小说没有后记,附录里是一篇访谈,题为《我的语言是黑暗的照亮》。他坦言:捎话的本意是沟通。那么,沟通的形式是什么呢?就像小说中那两个名为“妥”和“觉”的鬼魂,他们各自身首异处,又合二为一,在同一个身体里争吵不休,又最终和解。他们将以来世为人类捎话,或许只有不断地沟通与和解,才是与彼此及彼此的文化和信仰、与生灵万物及各自存在间的相处之道吧。
(《捎话》是一部由刘亮程所著的长篇小说,2018年10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发行。刘亮程,作家,1962年出生,居新疆。著有诗集《晒晒黄沙梁的太阳》,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在新疆》《一片叶子下生活》等,小说《虚土》《凿空》等,被誉为“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和“乡村哲学家”。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第十六届百花文学奖”散文奖,长篇小说《捎话》跻身“2018年收获文学排行榜”前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