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实而虚 轻而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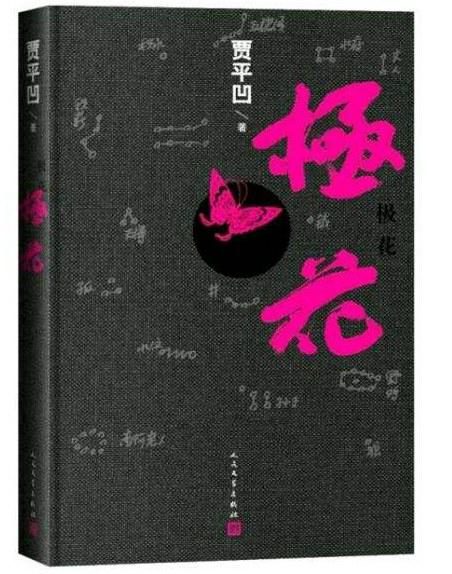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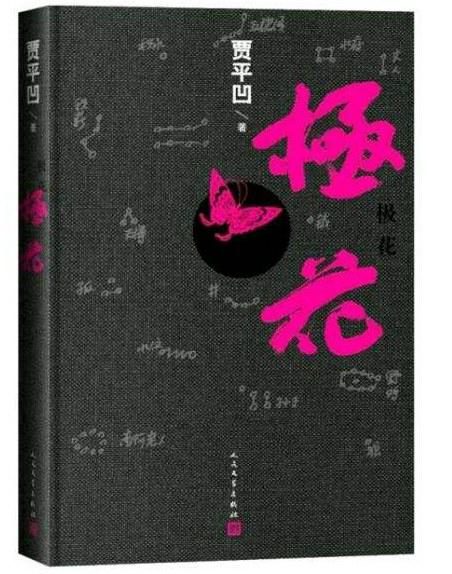
◇王俊
在这部不大同于以往的《极花》里,贾平凹依然在他探索性地写作道路上跋涉着,拿着历史的索魂棍和时代的探照灯,在乡间粪土与陈尸亡灵中索取着养分,以微弱的磷光照向这惶惑不安的当下和未来。如果说《带灯》中的带灯,还是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的萤火虫,那么《极花》里的胡蝶,却成了更加卑小低微的毛拉虫儿,到了冬日就休眠而死,夏天里,即便长成草开了花,也是要被晒干卖了的。
贾平凹的写作,一直都在一种矛盾的立场上理性而混沌地前行着,他的两难,似乎总在现代理性与传统伦理之间纠结着。这种纠结,并不是要做出一种终极的选择,而恰恰是和盘托出式地呈现这种两难的状态。也正因如此,贾平凹的小说构建,有轻重,有虚实,既有细碎,又有浑成,细碎而愈加浑成。《极花》就是一部于细碎中求浑成、越细碎越浑成之作。
《秦腔》以来,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就写得越来越密实,越来越多地以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来密不透风地构建着,但可以明显地看到,构建本身并不是他的本意——正如四面墙确实需要一块一块的砖混合着水泥沙子而垒起,但垒它的人并不仅仅是要垒四面墙、垒一座房子,而最终是要建造一个家园。贾平凹想要构建的,正是他广阔的意蕴空间。
如此,他虽然越写越实,却也越写越虚了——砖越垒越实,空间便越来越空虚充盈了,纤细而气益闳,填塞而境愈廓——仅在《极花》开头进入的前五段里,连“我”在内,就提及了11个人物之多,这种密实的主观的自说自话而实实在在的叙述,让人总得静下来再静下来才能听到“她”在说什么。可看着看着,你又会发现,务虚才是他的拿手好戏,“天上的星空划分为分星,地下的区域划分为分野,天上地下对应着,合称分野这你不知道?”
是了,贾平凹的述说就如同老老爷,一开始便认定了你是知道的,才说给你听。可其实,“我”还隔绝在一座幽闭的窑里,看不见什么星空分野。他在自己的神秘感、生存和死亡体验中,用务虚的笔法,写着这个偏僻、荒诞、穷恶的村子里,男人以如何的代价拐买着女人而女人以如何的血泪卑微地生存着,血葱如何繁盛而极花日渐稀罕,白云白得像白牡丹而土豆顿顿要填进肚子里去,刻石寄托着沉重的现实而剪花通灵般纤巧轻盈。在这样的故事里,他依然不忘提及那些如今已经消失许久的野物——狼、狐狸、野马、野驴、黄羊和獐子,它们在这里还没有消失。它们让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紧密相连。这也足以窥见写作者的内心,依然保存着对世界、对死亡、对大自然、对神秘事物的一种敬畏。
敬畏心重如山石,他的笔触却轻如干花,可以随空飘荡,也可以顺风顺水;思考和要承载的东西越来越重,就重如瀑布,让每一个读者,也成了他那样,像是“拿碗在瀑布下接水”。
我们都是时代的焦渴症患者,怎么接,都是不满,不去接,又焦渴难耐。我们的碗,负担不起这么宏大这么一泻而下的气势,负担不起时代的泄洪之水。我们只能退而远观,“遥看瀑布挂前川”。
“现在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兴时一种用笔很狠地、很极端地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年代的阅读吧,但我却就是不行。我一直以为我的写作与水墨画有关,以水墨而文学,文学是水墨的。”(《极花》后记)一张瀑布挂在那儿,要追求中国式的真实,就得写意。写意是水墨画的本质精髓,它既不是理性的,又不是非理性的。
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如何就有了“将物质写实与精神抽象相平衡、相综合的大气象”(谢有顺语),从来就不只是两难的问题。虽然,小说中的胡蝶最终面临了两难:她是要娘还是要孩子?如果娘有了孩子,而她的孩子又没了娘。这是一个荒诞的寓言。在中国这几十年的进程中,我们是要保住传统的根茎、文化的源泉,还是让时代的车辙碾压而过,顺应一切发展的趋势而动?我们是要倾听上一代的哀声,还是着想下一代的未来?是什么,把这看似对立的二者纠结在了一起?
贾平凹的如椽之笔,不是在被动地做着选择题,而是深具对于现实的反问能力——“我们的作品里,尤其小说里,写恶的东西都能写到极端,而写善却从未写到极致?”反问而没有答案,他只是依然真力弥满,拿捏着虚实轻重,笔法于老辣中见温柔,于温柔中见辛酸。
《极花》中,别处有极草,这里有极花;它索蝶而去,又濒临绝迹;那个已故的生出了黑亮的女人,却长得干净,性情安静,是个“人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