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私语总是一种诱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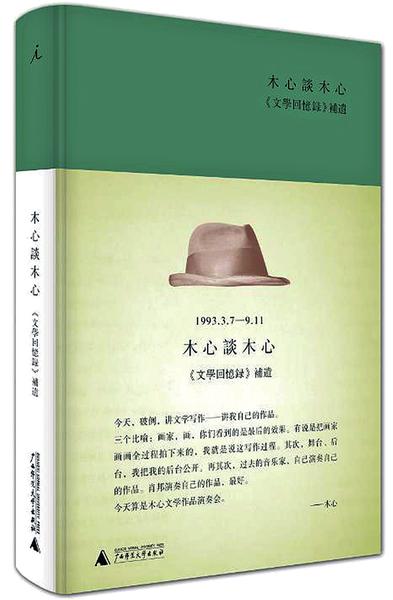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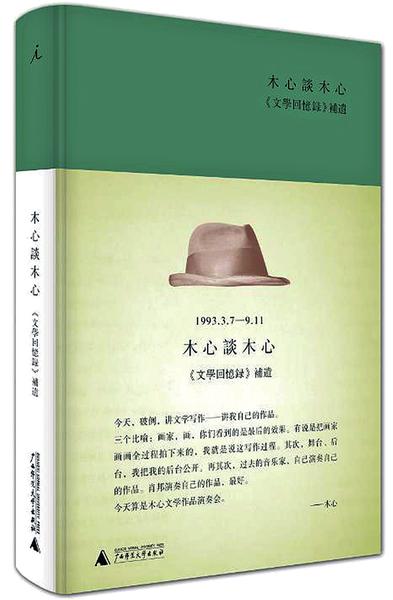
◇俞耕耘
当口腹之欲不满于餐厅菜谱时,私房菜出现了;当探求之心超出作品文本时,私房话出版了。《文学回忆录》重视“口述”这种“潜文本”存在,以笔录进行“赋形”,使私语成为作品。《木心谈木心》在三年后脱离“母体”作为补遗出版,陈丹青也在后记中道出了原委与顾虑。谈人易,说己难。木心很清楚自谈文章有如“鸡肋”,言重不免落入“狂狷”自夸,言轻又毕竟不那么甘心。而在众人“撺掇”之下,他终于谈及创作、访谈的个人“印象”。陈丹青也如木心,在读者的期待下,终于使回忆录“山水合璧”。他再一次“完成”了木心,将述而不作变为一本活泼泼的文艺讲稿。
木心所谓的“私房话”,正如魔术解密一般,掀开了作品的正面“台幕”,展示了创作的“后台”。他戏称“这是不公开的。最杀手的拳,老师不教的——写作的秘密。”如果说《文学回忆录》是“补药”,那么这本《补遗》正是“特效药”。特效是由于文章评点的“对症性”和“治愈系”。
在书中,它体现为作文之“技”与人生之“道”的统一。木心谈作文,并未拘于文本的封闭结构,而是传达了“作文如说话”的理念。写作的技巧与说话相通,说话又要基于听的辨识。书中《即兴判断》代序与《仲夏开轩》两篇访谈,正是他以案例问答讲写作技巧的运思所在。作家谈访谈,恰如语言上的“太极”,有见招拆招,化凌厉提问于无形的形式技巧;更有谈诗论艺,集人生哲学于大成的“干货”内涵。比如回答的语敲双关、搭架取势、虚实迂回、轻重发力都是关乎访谈“破”与“立”的关节。谈话中,木心显然是以“反制”换“主导”,以一种解构的“自毁”策略使访者提问本身“问题化”,从而不答自破。因为“辩论本身是战争性的。有些访者逼得很厉害,弄不好会跌倒的”。写作又何尝不是一场作者逼问自己作出对答的战争?他以访谈隐喻作文之理,自有高见。
如果说访谈本身是技巧性的,那么书中散见的文艺观点、人生哲学则是思想性的。木心始终追求生存与艺术的同构,他延续了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不追求体系,而是以感悟见洞识,以诗性见理性。在创作上,他强调文章力度、厚度、密度与气度的结合,表达“平实、恳切、满含体温”的“温情”。他的创作心态有如罗兰·巴特式的“文之悦”,“写作是快乐的,醉心于写作的人,是个抵赖不了的享乐主义者”。而小说与散文的互融,看重序的独立价值则彰显了他独特的文体意识。木心以适度原则处理创作中诸多异质统一关系:如用词的雅与俗、选裁的繁与简、节奏的徐与急、章法的收与放、情感与思想、印象与主见。他以上跳的“精灵”譬喻文章的悠游潇洒、举重若轻,这正是道家“步虚”的写照。在空的地方游走,即是追求象外之象,“功夫在诗外,在画外”。
木心的评点与所选文章形成了一种“对话交往”的召唤美学。评点正如旁白,增补了文章没有的创作“潜台词”,它是全书诱惑的“面纱”。没有作家揭秘,散文的玄机、妙处甚至“狡黠”,我们何以知晓?可以说,私房话让我们重新发现了另一个木心。他甚至可以“因文生事”,以虚构融入纪实散文,以情感真实取代了历史真实。“大家写作不要太老实”。妙句偶得,佳篇重读时又难以抑制“自得之乐”,“这篇序,可传。和唐宋八大家比,不惭愧”。“这句子,鲁迅会喜欢的”。想显露又不可卖弄,文章和评点总在唱和对答中照亮了木心的“真诚”与“可爱”。讲文亦在悟道人生,“要留余地”、“要懂得自己脱身”浸透着道家盈虚有数的清醒。“不过才气太华丽,不好意思。现在我来写,不再这样招摇了。现在我写的诗,比那时朴素多了”。这正是渐入老境,藏锋抱朴、绘事后素的艺术人生。“当没有人理解你时,你自己不要出来讲”,儒家“不知不愠”的箴言让木心平和冲淡。
文本与言说构成作家生命的虚与实,显与隐。私语的诱惑,并不仅在于满足读者的“窥私”癖好,同时更体现了一种生存美学的追求:在高度复制的时代,任何作品都因作家本人生活风格的灌注而富有价值。《木心谈木心》这种“自话”形式,呈现了生气淋漓的在场、性灵即兴的机锋。它不仅是作者自谈作文、说话的技巧,更实现了反思的“内视”、自我指涉的言说,成为不断提升、重返自身澄明之境的修身艺术。
